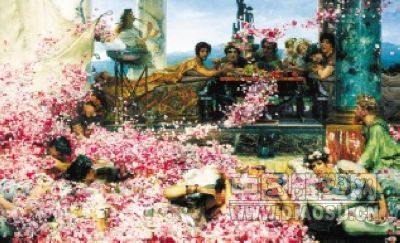
阿尔玛-塔德玛的《埃拉加巴卢斯的玫瑰》中,人体与玫瑰花瓣几乎融为一体,体现了画家极高的绘画技巧
上海美术馆展厅很少有这么多观众,却并不显得热闹,年轻人、孩子、老人,黑头发的,黄头发的——这样的机会对热爱艺术的人并不多见:莱顿、摩尔、柯罗、毕沙罗、蒙克……他们是19世纪古希腊艺术最忠诚的追随者,他们的画中有着一种“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”,包括这些大师作品的“古典与唯美——西蒙基金会藏欧洲19世纪绘画精品展”这些天在沪展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,人群是安静的,脚步是轻的,展厅里有种气场,让参观者迅速准确地找到了自己应有的精神状态:对美的虔诚。
这个将持续到8月20日的展览,无疑会让这个时间段内上海所有的艺术展览黯然失色。
记者手记
创作的门槛和欣赏的门槛
除了虔诚就是赞叹,这是多数观众面对上海美术馆展出的欧洲19世纪绘画大师珍品的感觉。古典与唯美的艺术,欣赏的门槛并不高。哪怕你并不清楚某一张画背后的宗教图式,不知道它的古希腊典故,甚至不知道画中的人是谁,当你站在那些栩栩如生的画像面前久久凝视,依然能看到那些女子眼波流转,在轻柔的光线下让人不知今夕何年。古典和唯美的艺术确乎有这样的魔力,它细腻的色彩和线条沿着画中人柔和的面庞身躯流泻而下,在你心里汇成一个安宁的深潭。而对于创作来说,这样的艺术就有极高的门槛。它不仅需要炉火纯青的绘画技巧,还需要虔诚——对艺术的虔诚,对美的虔诚,长时间进行某一种纯粹创造的专注。
我们实在很难相信,现在那些所谓成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有这么深厚的功底,可以画出这样直指人心的作品。我们也很难相信,批量生产作品甚至雇佣枪手的他们,还会愿意为了一幅作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。时间从来都是一种成本。在作品中支付大量的时间成本,作品会永恒。反之,则速朽。
用两三百年前的艺术标准来衡量当代的艺术家的确不公平,何况,艺术已经到了观念至上的时代。当我们在当代艺术的各个展厅里,看着各种需要大量文字阐释才能成立的奇怪作品一筹莫展时,艺术欣赏的门槛令人生畏。而在这个门槛的掩护下,一些故弄玄虚的艺术家则获得了大肆忽悠的辽阔空间。和古典与唯美时代的艺术掉了个儿,当代艺术创作的门槛降低了,而对观众欣赏的门槛则前所未有地抬升起来。这个门槛,不仅阻拦了普通观众的观看,也有可能将这个领域置于一个没有大众评价的灰色地带。
多么奇怪的现象,一群艺术家和一群策展人、批评家,自称以当代中国的各种现实为材料、以反思为己任、以探索为目标,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和活动,却自外于大部分人所构成的社会基本面,并且只要看过三次以上的当代艺术展览就会明白,他们的艺术和门槛外那个真实中国其实也没太深的关系。艺术和大众触目惊心地割裂,似乎就差一个明确的宣示:这是文化精英们觥筹交错的游戏,与你们无关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对古典与唯美的艺术的称颂,就不是艺术标准的倒退,而是对当代艺术的鄙弃。
早报记者 马俊 实习生梁佳
正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“古典与唯美——西蒙基金会藏欧洲19世纪绘画精品展”按历史时期与作品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分为四个板块:学院派与古典人体、浪漫风情与怀古、光与色的交响、劳动的赞歌。首次来华的这100幅绘画精品,藏品级别不亚于罗浮宫、大英博物馆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的藏品等级。而这些杰作的创造者们,都是西方艺术史上排名进入前一百名的大师。
在19世纪那样的年代,仰望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,任何的“写实模仿”均已成为技术上的重复劳作。自18世纪下半叶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以来,艺术迫切需要思想的解放、个性的尊重。于是,那些学院的传统和严格的限制反使艺术家的精力得以集中,并从狭窄的通道中释放出美丽。古典与唯美的艺术,诞生在照相术发明之前。但拟真并不是其终极目标,许多精心构图的画面,几乎就是一出神性和人性同台演出的剧照。画面凝固的是艺术家心目中某个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,一些戏剧性的元素、有象征意味的构图被安排进去,这个瞬间因此成为有价值、有故事的时间片断。古斯塔夫·多雷的《克劳迪娅之梦》题材取自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中的故事,作品不仅显现出画家的古典趣味,且选题独特,并没有局限于《圣经》中的重大题材。以历史、神话、宗教作为题材是古典主义的传统,而对女人体的赞美和欣赏使得古典主义透出一种柔美和精雅,弗雷德里克·莱顿笔下的“宁芙女神”身着宽大长袍,背对瀑布,深色的背景将女神白皙的肌肤映衬得温婉诱人,而女神古典式的站立姿势,让我们想起了古希腊雕塑中的维纳斯。
如果说女性之美是历来画家乐此不疲的选题,安德烈·佐恩则在当时做了大胆的尝试,《在沃纳划的船上》中的女人是位当地女青年,摆脱了古典主义对女性人体的美好幻想,较写实地描摹出略微下垂的胸部、隆起的小腹,颇有自然主义风格。但多数画家还是沉浸在“浪漫风情”和“东方想象”之中,这与当时“考古热”的兴起有关,在欧洲人的心目中,东方就意味着消遣、娱乐和感官刺激,而当时的女性地位也决定了“女人”在作品中出现的“观赏趣味”。《克娄巴特拉用死囚尝毒》讲述了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故事,在自杀之前,她下令让几个奴隶品尝不同的毒药,以便为自己选择痛苦最小的一种,她斜倚在兽皮长椅上,姿态闲适,观察着每个奴隶死亡时的表情,画面以外表的华丽与暗含着的死亡恐惧形成一种对峙的张力。
那么,除了欣赏美、得到感官愉悦之外,艺术究竟给生活增添了什么?在对形式美的狂热追求之后,古典美的巅峰已悄然而过。如果只有模仿,艺术的道路将从泥泞的沼泽沉寂地穿过。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后,画家将视角转向了普通百姓。《拾麦穗的女人》(朱尔·布雷东)、《第二次收获》、《收牧草的农妇》(朱利安·杜普荷)中的底层百姓则显得快乐、安详,显现出画家对农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,相对而言,莱尔米特和米勒的作品则更接近现实。
照相术、印刷术的发明,使古典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然而,对于艺术形式的探寻依然进行着,毕沙罗、雷诺阿、蒙克、劳特累克这些响当当的印象派先驱开始着力于光、影的探索,此次展出的多是他们的风景作品,从色块和笔触中,读到了艺术家的焦虑和不安,他们在寻找一个出口,一个新的转变,试图拯救艺术的消亡。
应该感激西蒙基金会,这个欧洲本土之外最大的艺术品私人收藏机构,是它把这些伟大的作品收集起来,并让这些作品从西蒙家族的墙壁上取下,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巡回。能够在上海美术馆的展厅里,隔着半米的距离观看那些作品,真是一种幸运。
发表评论
请登录